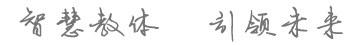| 您当前位置:自贡教体云平台 >> 教育管理 >> 基础教育 >> 浏览文章 |
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教育家精神
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教育家精神”
自21世纪以来,“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 成为当今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最热门的“关键词”。一流的教育需要一流的教育家,需要教育家们用一种深厚的教育家精神去成就学生、成就教师、也成就自己。时代呼唤教育家,教育需要教育家办学。但在当下, 关于中国有没有教育家、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家的问题一直成为社会和媒体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我们无法也无需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或固定的框架来确定哪些人是教育家、哪些人算不上教育家,也无需政府发一个文来“钦定”一批教育家,而是确立并弘扬一种教育家精神,让我们的办学者和教育者们用这种教育家精神去办学、去育人,从而使他们成为教育家。培养和造就教育家也就是培养、造就具备这种精神的人。 从“企业家精神”到“教育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已成为近年来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企业家精神,是指人们竞相成为企业家的一种态度和行为,意指“着手工作,寻求机会,通过创新和开办企业实现个人目标,并满足社会需求”。“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敢于冒险竞争的精神和敬业、永不满足的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某些方面,也许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人所具有的,他们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但是,他们却凭着这种精神,成为了他们各自所在的领域中的“佼佼者”。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尽管不为多数人所具备,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精神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则是越多越好。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能迅速从战争失败者的阴影中走出,变成世界经济的“强人”,“企业家精神”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批具备“企业家精神”人的涌现,会带动民族企业和国家经济的振兴。由此,笔者不禁想到,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振兴同样需要大批具备“教育家精神”的人来开创。中国自古是一个盛产教育家的国度。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便是开中国教育家办学之先河;汉唐时期的董仲舒、郑玄、王通和韩愈;宋元时代的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与陆九渊;以及明清之际的王阳明、王夫之、颜元,等等。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延续并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他们也用一种教育家精神照亮了文明古国教育发展的历程。20世纪以来,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黄元培、陈鹤琴、梅贻琦、张伯苓等为杰出代表的教育家,更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中国近代教育家们,一方面用他们的智慧和激情传承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同时,他们还用开拓的视野和创新的精神,吸纳着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改造和开创着一个现代的文化中国。可以说,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是由“五四”时期那一代教育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已历30余年,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之梦想,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崛起造就了一批新中国的企业家。同样,30年的教育改革也实现了中国教育跨越式的发展,但我们还不能自信地说,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批新时期的教育家。归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教育家”似乎是一个比“企业家”更难以界定的概念;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家”寄予了更多、更高、更大的期望,“教育家”身上承载着更伟大、更艰巨的历史使命,以至于我们不会轻易把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称为“教育家”。正因为“教育家”是如此沉重而神圣的一个称呼,所以很多杰出的教师和校长也自觉与“教育家”所应承负的使命和责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愿被人称为教育家。自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以来,一大批名师、名校长脱颖而出,虽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被正式封为“教育家”的头衔,但是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前辈教育家们所具备的那种精神和特质,这种精神和特质不仅造就了他们的办学业绩和教育贡献,也成就了他们自己。这种精神和特质就是一种“教育家精神”。 “教育家精神”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教育家?“教育家精神”到底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和内涵?目前学界和政界对此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这样几个因素作为衡量教育家的标准,如先进的办学理念、卓越的教育业绩、鲜明的教学教育风格、独特的管理模式、高尚的人格魅力、丰硕的科研成果、较高的影响力和较大的知名度等。其实我们都清楚,所谓的先进、卓越、鲜明、丰硕,包括影响力和知名度等,都是一些相对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因而,教育家及其教育家精神不是一个内涵十分确定的概念。尽管教育家及其精神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通过对历史上一些知名教育家的研究和对现实中一些名师名校长的调查,我们会发现在他们身上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精神特质,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共同的特质或因素造就了他们成为教育家或名师名校长,如饱满的激情、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高远的眼界、开阔的心胸、好学的精神,等等。笔者认为,教育家精神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来解读——— 满腔的激情,深沉的爱 教育家精神的基石 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爱默生曾言,无热忱便无伟大。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件伟大的事业不是因为热忱而成功的。大凡能够成为教育家的人,他们对教育事业终生都充满着满腔的激情。陶行知曾自我评价说,“我以出家入佛的精神从事着中国的乡村教育”。北大之父蔡元培也曾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以一种“入地狱”的精神完成对北京大学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这两位伟大的教育家都因为他们的激情和热忱而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和伟大。 当有人询问斯霞老师成功的秘诀时,她的回答是,“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全身心地爱着我的学生。”同样,于漪老师也告诉后人们,“教师要有满腔热情满腔爱,和学生心心相印!”正所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霍懋征老师正是用她的满腔激情、满腔爱造就了她成为新中国的“国宝”、一代教育家。通观中外教育的历史,举凡成为教育家者,都视教育为生命,对教育事业始终充满着饱满的激情。不求回报,不谋职位,而是把自己的生命价 寄予教育,把教育作为终生的追求。真正的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情感发自肺腑,是深刻而厚重的,而这种激情的持久且饱满是基于对学生的深切关爱而萌生。 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 教育家精神的“气场” 教育事业是事关人类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者必须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一切,以开阔的视野审视一切。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马寅初等教育先辈之所以至今令人敬仰与怀念,是因为他们以教育家的博大胸襟和视野,铸就了中国大学的宽容、民主、独立之精神。唯其如此,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助社会改良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正因为有着这种胸襟和视野,蔡元培在办北京大学时,明确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有了这种“自由”与“并包”,才有着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优秀学者的云集;有了这些人,才有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竺可桢在主持浙江大学时,也明确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像百川汇海,方成其大。大学为学问的海洋,应兼收并蓄,包罗万象”。正因为竺可桢办的浙江大学能够海纳百川,才有着后来的“东方剑桥”。 伟大的教育家都有着一个强有力的“气场”,进入这个气场的人和物都会受其感染和内化的。“大气”往往被视为博大胸襟和开阔视野“气场”的一种境界体现。因为只有“大气”才可以成就“大器”。北京四中刘长铭校长认为,“大气的教育首先来自教育者的理想、胸怀、远见与良知”。也就是说,没有教育者崇高的理想、宽广的胸怀、开阔的远见,就不会有大气的教育。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说,校长的大度和大气,让老师们感受到自由的愉悦,课堂上,他们会自信从容,神采飞扬。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则认为,“信仰是成长的价值皈依。有信仰就有精神家园,有家园就能安身立命,就能行当所行、止当所止,就能全神贯注、一以贯之”。信仰的高远是胸襟和视野的精神航标。大气的教育需要大气的教师。大气的教师温暖每一个学生,像霍懋征老师一样“从教60 年,从没有和学生发过一次火;从教60年,从没有请过一次学生家长;从教60年,从没有惩罚或变相惩罚过一个学生;从教60年,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过队。” 创新的意识,开拓的勇气 教育家精神的动力 早在上个世纪,陶行知先生就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对教育家精神提出了这样几点要求:“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教育也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在这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需要一流的教育家具备创新意识、开拓的勇气,这样才能探明“新理”,开辟一个新的“疆界”。今天,中国教育又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此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具备开拓创新精神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去探明、开辟、追求理想的教育。 创新的意识、开拓的勇气是成就教育家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放眼中外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教育家,他们都是因为具备着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和开拓的勇气,才在世界教育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孔子之于私学、柏拉图之于阿卡德米学园,到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苏霍姆林斯基之于巴甫雷什中学;从朱九思之于华中工业大学、刘道玉之于武汉大学,再到李吉林之于情境教学、魏书生之于民主科学教育,等等,都是一个个典型的案例。最近,教育部在《关于向霍懋征同志学习的通知》中便明确指出,要“学习她孜孜不倦、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霍懋征同志是一位自觉而勇敢的教育改革实验者,是新中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带头人和成功经验的创造者,是上世纪50年代就蜚声全国教育战线、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 所有有志于成为教育家的人都需要具备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开拓的勇气。 执著的追求,坚定的信念 教育家精神的航标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要想作出一番业绩,非短期能够奏效,需要教育者为此作出终生而不懈的努力。世界上所有在教育改革上有所贡献的教育家或教师,都是以10年、20年、30年甚至终生在与学生的零距离接触中脚踏实地地工作,终于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育理论财富。教育家不仅需要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时还需要一种定力和耐力——即执著的追求、坚定的信念,而且这种定力和耐力在当今浮躁、功利的时期显得尤其重要。这种信念与追求如航标引领、激励着教育者渐成为教育家。也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诫教育者们,“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生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 教育家必须具备坚定的信念。教育家的信念源于对社会、文化、教育和人自身的一种理性判断和认识,并且将这种认识和判断上升为个人的一种信仰和追求,并且身体力行。有了这种信仰和追求,他们自然会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才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教育家精神的灵魂 霍懋征老师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现在的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敬业精神、责任心和爱心。今天的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这点很多教师都没意识到。他们只是把教师当作职业,觉得把课教好就行了。教师必须要想得多一点儿,要想到不管多调皮的孩子,他都会长大成才,会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是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的大事业,需要教育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承载历史和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和职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看似普普通通的教育格言,却折射出霍懋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成为她教育的动力和源泉,是她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也是她一生的座右铭。 因为有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陶行知才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张伯苓才会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呕心沥血,从开办“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培育并发现“教育家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教育者,你也许不可能成为一名教育家,但不能没有对教育家精神的追求、不能没有成为教育家的意识。拿破仑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套用此言,笔者想说,不想成为教育家的教师、校长不是一个好教师、好校长。也许,我们永远也达不到教育家的彼岸,但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把它作为引领我们前进的航标,即使我们一辈子不能成为教育家,但是我们对“教育家精神”的追求和向往一刻也不能停止。在今天这个教育家匮乏、呼唤教育家、需要教育家、造就教育家的时代,在短时间内,我们可能还不能培养造就出千千万万的教育家来办学,但是我们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个具备教育家精神的 教师和校长来办学、执教。 首先,我们“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着力弘扬、宣传中外教育家(尤其是本土教育家)及其精神,形成一种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营造、培育一种有利于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成长和发育的外在环境和氛围。当年,武训“行乞”办学的精神曾被搬上银幕;如今,《孔子》已经被拍成大片,《张伯苓》《黄炎培》已走入电视剧中;孟二冬、殷雪梅也分别被搬上了银幕……这些无疑对弘扬一种“教育家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还有许多教育家不仅其人生极富传奇色彩,而且精神高尚、个性鲜明,十分适合搬上银幕的,如蔡元培、陶行知、竺可桢、马寅初、梅贻琦等;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教育家如霍懋征、斯霞、于漪、刘道玉、魏书生等,又何尝不能成为银幕中的“英雄”?! 其次,我们要加强对现当代依然健在的教育家的思想与精神的研究。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教育艺术和教育家精神等方面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难得的宝贵精神和文化财富,加强对这些宝贵财富的研究、发掘和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前,我们往往注重对已经去世的教育家的研究和发掘;其实,加强对健在的、至今仍然活跃在教育界的教育家、名师名校长以及优秀教育工作者们的思想、行为、成绩与精神等方面的研究、发掘、整理,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后人们的成长与发展都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其次,我们还要加强对教育家精神的发现和发掘。可以说,培养、造就教育家就是培育和发掘教育者身上的这种“教育家精神”。假如这种精神和特质是天生就有的,或许是无法培育的,那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校长培训机构是否要考虑到,要选拔具备这种精神特质的人来担任教师和校长。正如西方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得好,你可以教会一只鹦鹉去爬树,但最好还是选择松鼠。因此,我们需要用发现的眼光,发掘赋有这种精神特质的人来从事我们伟大的教育事业。 “教育家精神”需要培育,也需要发现。
在今天这个教育家匮乏、呼唤教育家、需要教育家、造就教育家的时代,我们可能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培养造就出千千万万的教育家来办学,但是我们可以培养成千上万个具备教育家精神的教师和校长来办学、执教。 (厡载2010年6月15日《中国教育报》第5版) 相关阅读
|